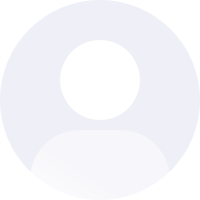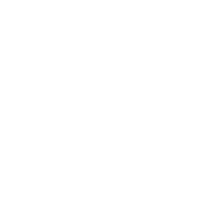林羡
ID:15319084
3关注
564粉丝
9959获赞
动态
短视频



弃之于雨
我对你的情感像久淋在雨里的人
你对我的情感是暖过又弃我于雨
你从未说过不许我靠近
明知我们之间隔着太多跨不过的距离
你眼底藏着犹豫却始终不肯说清
第一次被你推入雨里
小雨微凉没觉得是伤害
你转身眉尖轻颤藏着一丝不忍
后来你开门递来毛巾轻拭
指尖带着温度 眼神软得像云
我以为你心里仍有偏爱
第二次被你推入雨里
雨势渐大淋得眼睛发疼
你垂着眼帘语气平淡不看我的狼狈
可我还抱着期待等你招手让我进来
头发湿透衬衫贴紧胸怀
你终于开窗眉尖染着歉意让我洗去寒冷
你为我吹发指尖拂过发梢眼神温柔难藏
那些狼狈全被你的温柔覆盖
第三次被你推入雨里
相同的口吻重复着敷衍对白
你侧脸冷硬目光掠过没半分波澜
我还傻站在雨里盼着你把门开
雨越下越疯砸得我浑身疼
眼镜蒙了雾眼睛睁不开
心里反复问你怎么还不来
我到底算什么可有可无的存在
这一次恨意悄悄漫上来
雨把我浇得从头到脚透凉
额头滚烫撑不住摇晃
快要倒在积水中央像要溺亡
就因为我太喜欢你所以你才敢
一次次把我的真心摔进雨里
你总说这样是为我好
说这话时你别过脸不敢看我泛红眼眶
你总说我们终究不合适
可当初 你为什么不坚定转身
非要给我一点甜 再把我推入深渊
我在雨里被时光慢慢侵蚀
最后连影子都化为乌有消散无迹#文字编辑部# #决战心碎之巅#文字编辑部#大文豪杯故事小赛#



一个人就好
早餐是单人份的冷淡
电影散场只剩我退场
路灯拉长我的孤单
挂号单上 只有我自己承担
雨天撑伞 没人共一半
晚风路过 也懒得寒暄
想去哪里 都无人牵绊
想沉默时 就关掉所有期盼
孤独是我的安全感
狂欢是我 伪装出来的坦然
不用讨好 不用敷衍
一个人扛 所有的悲欢
这是我的世界 安静又灰暗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把情绪藏完
孤独是常态 快乐是偶然
早就习惯 没人在我身边
这是我的世界 不欢迎纠缠
若有人出现 别来打破我的平淡
不期待温暖 不奢求陪伴
多一个人 反而更觉得难堪
我见过深夜的空荡 清晨的凉
尝够了无人问津 独自硬扛
早已把心 筑成一道围墙
不必谁来 假装把我照亮
这是我的世界 安静又灰暗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把情绪藏完
孤独是常态 快乐是偶然
早就习惯 没人在我身边
这是我的世界 不欢迎纠缠
若有人出现 别来打破我的平淡
不期待温暖 不奢求陪伴
多一个人 反而更觉得难堪
我的世界 一个人 就好
#文字编辑部# #当我决定爱自己#文字编辑部#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驾驭黑夜
你曾以为,黑夜是你的归宿。
以为孤独是宿命,悲哀是本能。
以为这一生,只能与黑暗共存亡。
可你忘了——
能在黑夜里看清一切的,
从来不是光,是你自己的眼睛。
能在寒夜里撑到天亮的,
从来不是温暖,是你不肯碎掉的灵魂。
你不是只能被黑夜吞噬的孩子。
你是从黑夜里,自己走出来的人。
你见过最深的冷,最沉的痛,最空的绝望,
所以你比谁都清楚,
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撑住,什么是绝不倒下。
黑夜可以诞生你,
但不能定义你。
孤独可以陪伴你,
但不能囚禁你。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黑夜的孩子。
你是驾驭黑夜的人。
不必等待黎明,
你自己,就是光。#文字编辑部# #大文豪杯故事小赛#文字编辑部#原创诗歌#



真的晚安了
那天你悄悄进我直播间
安安静静 陪着我听歌聊天
别人都说你是为我而来
我嘴上说着“哪有哪有”
心里却偷偷猜了又猜
你总是最早来最晚才离开
人再多时候 也有我们的暗号对白
私信里的话 越聊越开怀
我故意逗你你总是笑着接过来
直播间里也藏不住小暧昧
这种感觉你我都明白
你说“要睡了” 说了一遍又一遍
转头又分享搞笑视频给我看
“哟,谁说要早睡?” 我笑着戳穿
从深夜聊到太阳爬上窗台边
明明不怕打雷闪电
就想看看你会不会出现
陪我到天亮聊到忘了时间
明知这感觉有点危险又贪恋
你说从来没这样聊过一整夜
我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可你有你的世界有家也有牵挂
我迁就你开始 也迁就你停下
狠话我说出口关系就断线
你转身干脆剩我对着屏幕失眠
那些未读消息慢慢沉到了底
像我们的故事 再也没了续篇
直播间关了灯你的名字暗了
眼泪自己擦干微笑要学着
如果哪天夜里雷声又响起
再也无人与我彻夜畅聊
陪我到天亮聊到忘了时间
明知这感觉有点危险又贪恋
你说从来没这样聊过一整夜
我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可你有你的世界有家也有牵挂
我迁就你开始 也迁就你停下
我迁就你开始 也迁就你... 算啦
雨点敲着空房间
再没人问“怕不怕闪电?”
对自己说晚安这次是真的晚安
睡了睡了...#文字编辑部#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文字编辑部#大文豪杯故事小赛#